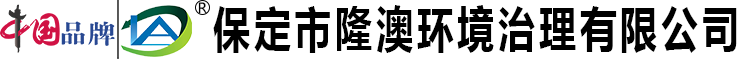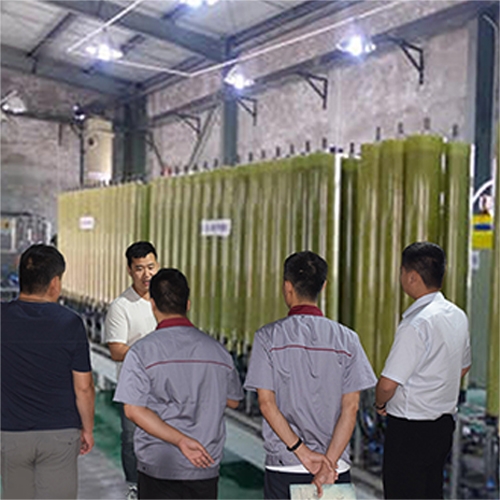如果说政治压制让百姓感到窒息,那么王室的腐败则让百姓感到恶心,并最终抽干了政权合法性的最后一滴血。虽然国王本人勤于政务,但他背后的庞大王室家族就像寄生在国家动脉上的吸血鬼。
巴列维家族拥有63名核心成员,在石油财富滚滚而来的年代,这些王子公主和皇亲国戚们把国家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。他们利用特权倒卖石油合同,垄断进口贸易,从每一个大型基建项目中抽取巨额回扣。当时流传着一个公开的秘密,任何外国公司想在伊朗做生意,如果不给王室成员送上干股或佣金,合同就别想签下来。据后来的统计,王室家族在海外的资产高达数十亿美元,而这一切都毫无掩饰地展示在公众面前。在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,王室成员和依附于他们的权贵们过着奢靡的、令人咋舌的生活,他们用黄金打造马桶,从欧洲空运鲜花和矿泉水,在私人飞机上举办狂欢派对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德黑兰南部贫民窟里刚刚进城的农民正为了几块大饼而发愁。
面对沸腾的民怨,国王也曾试图反腐,他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,甚至抓了几个高官做样子。但这注定是一场闹剧,因为腐败的根源就在王座旁边,国王不可能抓自己的亲姐姐,也就是被公认为“交易女王”的阿什拉夫公主。当反腐变成了只打苍蝇不打老虎,甚至变成权贵之间互相清算的工具时,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便彻底崩塌。这就是1970年代末伊朗的真实写照,经济上,它像一列高速飞驰的列车;政治上,它像一辆甚至没有刹车的破旧马车;道德上,它已经千疮百孔。那些曾经从白色革命中受益的农民、工人和中产阶级,看着被权贵切走的巨大蛋糕,看着无处不在的特务,心中的感激早已变成了仇恨。国王感觉自己很委屈,我给了你们面包和工作,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对我?但他不懂,当一个政权失去了公正,再多的面包也填不满人心的黑洞。当最后的支持者,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也转过身去,波斯雄狮的末日也就到了。
当历史的大船即将沉没时,最先跳水的往往不是底舱的苦力,而是住在头等舱的乘客。
1978年的下半年,伊朗就上演了这样一幕真实而残酷的泰坦尼克号效应。巴列维国王用石油美元精心培育出来的中产阶级,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跑得比谁都快。这群人是现代化最大的受益者,他们住着带泳池的别墅,开着欧美进口的轿车,孩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。按理说,他们应该是世俗政权最坚定的捍卫者,但事实恰恰相反。在精神上,他们极度厌恶国王,厌恶腐朽的君主制,痛恨无孔不入的秘密警察,更看不惯王室的。所以,当街头运动起步时,很多中产阶级其实是抱着同情甚至支持的态度。他们天真地以为这只是一场要求民主和自由的运动。然而,当局势开始失控,街头的口号从要民主变成了至大,当焚烧电影院和银行的火光照亮夜空时,中产阶级害怕了,但他们没选择站出来组织力量对抗暴民,也没选坚定地支持国王维持秩序,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于本能的选择——逃跑。
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,德黑兰的梅赫拉巴德机场每天都挤满了人,那是伊朗的精英阶层,有医生、工程师、教授、大商人。他们变卖了能带走的一切资产,换成美元或黄金,拖家带口地飞往伦敦、巴黎和洛杉矶。这是一场可怕的社会蒸发,就好比一锅烧开的水,最活跃、最有能量的水分子——精英和知识分子率先蒸发逃逸了,留下来的只有越来越浑浊的沉淀物。跟着社会中坚力量的离场,伊朗社会失去了缓冲地带。一种原因是早已失去民心的政府,另一方面是愤怒且被宗教狂热点燃的底层民众,两者之间再也没理性的中间层来调和,大崩溃已经不可避免。
1979年1月,绝望的巴列维国王含泪登上了飞往埃及的飞机。他前脚刚走,看似强大的帝国防线就如雪崩般垮塌。
最先倒下的是军队。巴列维拥有一支号称世界第五强的军队,装备着当时最先进的美国F-14战机。但在革命面前,这支军队却像纸糊的一样脆弱。原因很简单,军队的脑袋是世俗的,但身体是传统的。高级军官们是国王提拔的,享受着高薪厚禄,生活西化,但几十万普通士兵却来自贫穷的农村,他们从小在寺长大,对宗教领袖有着天然的敬畏。当霍梅尼发出号召,要求士兵回到的怀抱,不要向兄弟开枪时,军队的指挥系统瞬间瘫痪,士兵们拒绝执行命令,甚至把枪口转向了军官。在很多军营里,士兵们扔掉帽子,戴上鲜花,加入了的队伍。
而在巴黎流亡的霍梅尼展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。在革命成功之前,他住在巴黎郊区,每天在苹果树下接受西方记者的采访。那时候的他看起来像个慈祥的长者。他向世界承诺,未来的伊朗将是一个民主国家,他自己不想要权力,只想做一个精神导师,甚至承诺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穿着。这些话不仅骗过了西方政客,也骗过了伊朗国内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。大家都以为,赶走了腐朽的国王,就会迎来一个更自由的春天。
但当1979年2月霍梅尼乘坐法航降落在德黑兰的那一刻,一切都变了,雷霆手段迅速取代了民主承诺。随着权力的稳固,新政权迅速确立了七个反对的原则,全面切断与西方文化的联系。世俗法律被废除,取而代之的是严苛的宗教法;那些曾经和霍梅尼并肩作战的左翼人士、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快被逮捕或处决,伊朗世俗化的大门轰然关闭。
在这场变局中,最令人心碎的画面莫过于那些伊朗女性的命运。就在几个月前,她们还在临海的沙滩上穿着比基尼晒太阳,在迪斯科舞厅里跳舞,在大学里和男同学争论哲学。她们以为这种自由是与生俱来的,就像空气一样自然。但一夜之间,寒风袭来,街头慢慢的出现手持棍棒的道德警察,强制佩戴头巾的命令下来了,口红和指甲油成了罪证,男女混校被禁止。
当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试图反抗时,她们惊恐地发现了自己是如此孤立无援。那些曾经和她们一起喝咖啡、谈论萨特和波伏娃的男性精英们当中,有能力的男人早就飞到了欧洲和美国,在异国他乡感叹故土的沦陷;没能力的男人为生存或出于从众心理,蓄起了胡须,换上了深色长袍,默默接受了新的规则。更糟糕的是,还有无数来自底层的男性,他们正因权力的翻转而狂欢。在这个新秩序中,他们通过压迫女性获得了某种扭曲的满足感。于是,那些曾经明媚鲜活的伊朗女性只能独自面对狂热的浪潮,她们眼睁睁看着自由的大门在面前关上,从此被锁进那层黑色的布料里,一锁就是半个世纪。
1979年革命胜利后,霍梅尼曾向民众描绘过一个美好的乌托邦。他承诺,在这个新的共和国里,不但要有精神的独立,更要有物质的富足。那时最著名的口号是「石油收入将直接摆上每个伊朗人的餐桌」。他还许诺过免费的水、免费的电,以及给穷人免费的住房。然而,半个世纪过去了,当年的承诺不仅没能实现,整个国家反而陷入了一个不能自己的死局。这个死局的根源在于,这套政教合一体制存在某些先天不足,就像一台被装错了操作系统的电脑,无论怎么升级硬件,都无法运行现代经济这套复杂的程序。
首先是意识形态对经济的限制。新政权确立了「不要东方,不要西方,只要」的外交原则,这听起来很硬气,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,这等同于自杀。现代工业体系需要全球分工,需要引进技术,需要国际市场。但伊朗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,与美国长期对抗,一直处在自我孤立或被制裁的状态。它的石油卖不出去或者只能打折卖,它的工厂买不到零件,甚至连客机老化了都买不到维修配件。一个只有9000万人口的市场是无法在封闭状态下维持高质量的工业循环的,所以伊朗的经济和工业发展一直受限。
其次是教法与市场的根本冲突,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契约精神、银行利息和保护私有产权,但这么多东西往往与传统的教法存在摩擦。比如,为符合教法禁止高利贷的规定,伊朗的银行系统变得极其复杂和低效,导致企业融资困难。更严重的是,为了控制经济命脉,伊朗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怪胎——骨干基金会。这些基金会名义上是慈善机构,其实就是由宗教领袖直接控制的商业巨头,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巨型国企。它们控制了伊朗经济的半壁江山,从石油、建筑到甚至软饮料无所不包。关键是,这些基金会不需要纳税,也不接受政府审计,只对最高领袖负责。他们利用特权挤压非公有制企业。一个普通的伊朗商人生意做得再好,一旦做大,就会碰到这层教法天花板。如果他不愿依附于宗教权贵,他的生意就做不下去,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割足适屡。为维护神权体制的纯洁性,必须牺牲经济发展的逻辑。
如果说体制问题是慢性病,那么内政外交的全面透支就是现在的急性大出血。虽然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,但这笔钱并没有用来改善民生,而是被两个巨大的黑洞吸干了。
第一个黑洞是输出革命。为了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,伊朗长期奉行输出革命战略。从黎巴嫩的到也门的胡塞武装,再到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,伊朗每年都要向这些海外盟友输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物资。对于德黑兰的战略家来说,这是构建什叶派新月的必要代价。但对于吃不起肉的伊朗老百姓来说,这是在割他们的肉去喂别人的狼。
第二个黑洞是庞大的维稳成本。革命卫队不仅是一支军队,更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。为维持政权安全,国家必须供养庞大的军队、警察、民兵和情报机构。这一内一外两个黑洞彻底掏空了伊朗的国库。这种透支带来的后果是对政权基本盘的残酷反噬。而霍梅尼最忠实的支持者,是被称为受压迫者的底层贫民,在革命初期他们确实分到了一些好处,比如各种食品补贴和能源补贴;但现在,由于国库空虚,政府再也发不起补贴了。为了填补赤字,政府只能印钞票,结果就是恶性通胀。官方多个方面数据显示,通胀率已超越40%,但实际感受远高于此。
通胀是对穷人最狠的掠夺,那些曾经在这个体制下获得一点点尊严的底层民众,现在发现了自己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如果是在20年前,伊朗人可能还会寄希望于改革派总统,那时候人们会去投票,希望选出一个温和的领导人,稍微放松一点管制,稍微搞好一点经济。但现在,伊朗社会对于现状已经绝望,年轻一代们认为,无论换谁当总统,只要在这个神权体制的框架内,伊朗的命运就不会改变,所有的改良路线都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伊朗的崛起与堕落不单单是一个遥远中东国家的悲剧,它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那些残酷而普遍的规律。为什么巴列维王朝拥有那么多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、那么多优秀的经济学家、工程师和艺术家,最后却败给了甚至有些文盲的底层民众?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社会学真相,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不取决于它最高的那部分人飞得有多高,而是取决于它最基础的那部分大众站在哪里。用统计学的话说,精英代表的是方差,而大众代表的是均值。在1979年的节点上,德黑兰的精英们已经在思考后工业时代的议题,他们在讨论存在主义哲学,在规划核能发电。然而,在广袤的农村和城市的贫民窟里,绝大多数伊朗人的认知还停留在几百年前,他们听不懂复杂的经济理论,也不关心什么是世俗主义,他们只听得懂寺里的布道。当这两个群体的认知差距大到无法弥合时,悲剧就发生了。
历史告诉我们,国家的走向最终是由认知的均值决定的。当精英们试图强行把国家拽向一个大多数人没办法理解、也无法适应的高度时,绳子就会断裂,反作用力会把整个国家重重地摔回地面。那些超越了时代的先觉者往往结局悲惨。伊朗的许多知识分子和自由派人士,他们看清了方向,但跑得太快,把人民甩丢了。如果不愿沉默,他们就要为整个族群的认知短板买单。在革命后的清洗中,那些最聪明的大脑、最热诚的心灵,要么流亡,要么倒在了枪口下。这是一种先觉者的悲歌。
伊朗的历史还无情地粉碎了许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进步史观。大多数国家的教育往往暗示我们,历史是螺旋上升的,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,现代文明一定会战胜传统愚昧。我们以为这是一条单行道,一旦迈过了现代化的门槛,就不会再退回去,但伊朗用它的血泪史告诉我们,这不是真的。历史是非线性的,就像科幻小说《三体》里描述的那样,和平繁荣的恒纪元只是短暂的侥幸,混乱无序的乱纪元可能才是常态,如果处理不善,现代化的大门是随时有可能关闭的。
看看那些1970年代伊朗女性的照片,那不是对未来的想象,那是确凿发生过的历史。谁能想到一个已拥有核电站、汽车工业,甚至计划举办奥运会的国家,会在几年内崩溃瓦解,然后走上政教合一的道路?
文明是极其脆弱的,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遗产,而是一份需要小心呵护、时刻警惕才能保住的契约。虽然现在的德黑兰依然笼罩在严冬之中,虽然女性依然要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露出一缕头发的权利,但这个古老的民族有着惊为天人的韧性。物理学的规律告诉我们,当一个高压锅里的水持续沸腾,而盖子又被死死捂住时,结局只有一个,要么盖子被掀翻,要么锅被炸裂,那个时刻终将到来。只是,当我们凝视这头伤痕累累的波斯雄狮时,心中免不了感到悲凉,因为它为了证明那些本该是常识的道理,已经流干了太多的血,错失了太多的时间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加多